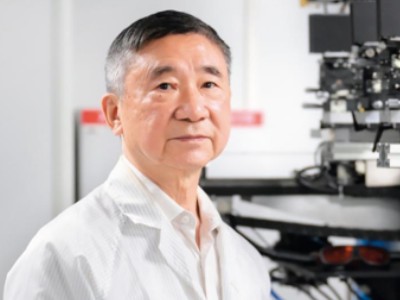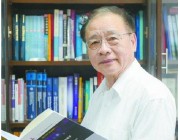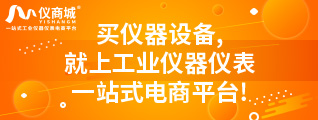四大光機所是我國光學事業的發源地,也是最早的光學體系根基。他們像母親河一樣,源源不斷地向全國各地輸送著光學人才。在四大光機所里,有很多有趣的人和事,正是他們的努力,奠基了我國光學事業的如今蓬勃發展。我們將從祖國的西邊開始探尋。本期,讓我們一起走近中國科學院西光所首任所長龔祖同院士。
我是一個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學科研,耳聞目睹,在我心靈中形成這種觀念: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唯有科學技術是建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
——摘自龔祖同1979年1月《入黨志愿書》

1984年8月,龔祖同審查設計方案
西渡東歸:所學所研專業為國所需所用
龔祖同,1904年11月10日生于上海市川沙縣一個小學教師家庭。幼年隨父親上小學常過黃浦江,看到滿江都是外國輪船,心里很難過,總想著哪一天江上的船能飄揚中國國旗。此時的他已在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科學救國、實業興國的種子。1926年龔祖同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帶著母親以土地作抵押借來的錢和科學救國的強烈愿望邁入清華園。1930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任教。1932年進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我國實驗核物理先驅趙忠堯。
1930年,趙忠堯完成實驗的結論震驚了當時的物理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后來的實驗更讓他成為世界上首次發現反物質的物理學家。
1932年到1934年,龔祖同作為趙忠堯的研究生,對二次γ輻射做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伴隨硬γ射線反常吸收的二次γ輻射的波長》和《趙忠堯、龔祖同致Nature雜志》,對趙忠堯發現伴隨硬γ射線反常吸收的二次γ輻射之后國際學術界在理論上所做的不同推測和解釋做了實驗驗證,并指出Thcγ射線的瑞利散射并不存在。
正當龔祖同在實驗核物理的前沿取得初步成績并滿懷信心開拓前進時,祖國的需要改變了龔祖同的科學生涯。
“九一八”事變后,戰爭的烏云籠罩華北。時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的葉企孫,看到對軍事極為重要的應用光學國內尚屬一片空白,十分焦急。1934年,留美公費考試中恰好有一名應用光學名額,他決定動員刻苦鉆研并初露鋒芒的龔祖同去報考。他對龔祖同說,應用光學在國防上很重要,我國還是空白,留美公費考試中有一個應用光學名額,望能報考。
“是空白,我就去填補。”龔祖同毅然接受了這個決定他一生專業方向的提議,被錄取為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應用光學直讀博士學位的公費生。但后來,導師趙忠堯指出,德國光學在世界上領先,不一定去美國。龔祖同接受了這個建議,于1934年夏,經西伯利亞去德國柏林技術大學(現稱柏林工業大學),開始了他研究應用光學的生涯。
1936年,龔祖同以 “優秀畢業生”的榮譽自該校畢業并獲特準工程師稱號,隨即在應用光學專家F·維多特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工程博士學位的論文工作,題目是“光學系統高級球差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意義在于開始了我國高級像差的研究,并為把光學設計引入我國奠定了基礎。
1937年底,他博士論文完成且行將答辯。這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內要他盡快回國籌建軍用光學儀器工廠。1938年初,他放棄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毅然回國,投身抗日戰爭,參加我國第一個光學工廠——昆明兵工署22廠,也稱為昆明光學儀器廠的組建工作,決心為前線將士制造一批雙目望遠鏡。
開創眾多第一:為中國應用光學領域
第一批軍用望遠鏡。龔祖同采用德國的設計技術,使用當時國內僅能找到的一臺電動計算機,很快完成了制造雙目望遠鏡的光學設計的第一關,在克服日本侵略帶來的物質條件上的種種困難后,僅用了半年多時間就制造出了中國第一批軍用雙目望遠鏡,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龔祖同的這項工作不僅實踐了他科學救國的理想,也與當時遷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嚴濟慈、錢臨照等試制顯微鏡的工作一起,開創了中國近代光學設計與光學儀器制造的歷史。
在完成雙目望遠鏡的試制、生產后,他又試制了機槍瞄準鏡,參與試制了倒影測遠機。
第一架紅外夜視儀。1958年,依據新中國的國防安全急需,龔祖同指導研究生王乃弘試制成功中國第一只紅外變像管并制成了中國第一架紅外夜視儀,隨后推廣至云南光學儀器廠,武裝了火炮及重機槍。1960年又試制成功使用多堿陰極的可見光靜電聚焦三級串聯像增強器,用于被動式微光夜視,即一種無需照明、僅依靠微弱的月光及星光觀察的夜視技術。這開創了中國的夜視技術的歷史,為我國微光夜視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8-1960年,龔祖同主持研制成我國第一臺透射式電子顯微鏡。
另外,1960年,龔祖同擔任研制2.16米天文望遠鏡的技術負責人。隨后為其中間試驗品60 cm望遠鏡的設計、加工、裝調奔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項工作拖延了17年。由于龔祖同促進修改,最終于1976年成為一臺有用的望遠鏡。這項工作為制造中國的天文望遠鏡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西光所原科研處長陳中仁研究員追憶講述,“遺憾的是,當2.16米天文望遠鏡于1989年矗立在河北省興隆縣山上開始探索宇宙的奧秘時,龔祖同已經與世長辭。”
熔煉出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龔祖同深知,不能生產光學玻璃,光學工業難為無米之炊。依靠進口玻璃,中國的光學工業不可能真正獨立。因此,從依靠進口光學玻璃制成軍用雙目望遠鏡起,自行生產光學玻璃就成了他魂牽夢繞的目標。
1939年冬,龔祖同用自己公費留學節省下來的400英鎊及同學的資助,于1940年初開始在上海小規模試制光學玻璃。由于重慶國民政府設法營救,龔祖同得以喬裝逃出上海,返回昆明。第一次試制光學玻璃失敗。
1942年,他到貴陽紅巖沖建造簡易廠房,開始試制光學玻璃。但在日本投降后,當局者認為光學玻璃可以從美國進口,自己不值得搞,因而撤銷了貴陽試制廠。龔祖同第二次試制光學玻璃宣告失敗。
1945年10月至1948年 ,龔祖同千方百計利用各種資源和機會,輾轉南北各地,分別在秦皇島耀華玻璃廠、上海耀華公司試制光學玻璃。而這第三次試制光學玻璃的愿望又成了泡影。幸運的是,他在上海耀華廠認識了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王大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大珩任中國科學院長春儀器館館長。1950年,王大珩從東北人民政府申請了40萬元撥款,邀請龔祖同去長春攻關。
知難而進,屢敗屢戰,龔祖同日夜生活在爐邊,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1952年除夕,第一次獲得了300升(一大坩堝)K8光學玻璃。接著又成功了兩坩堝。
歷盡艱辛,他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宏愿,開創了中國自行生產光學玻璃的歷史。接著是鞏固、提高,開發新的品種。由硼冕玻璃到火石玻璃,再到鋇冕玻璃。在工藝上從經典法發展到澆鑄法。與此同時,他們向全國各地提供了圖紙以解決國內急需,他們有時甚至把自己的試制車間供工業部門生產之用。
中國的光學玻璃工業從此誕生。
從1951年春提出光學玻璃試制車間的規劃到1958年轉而研制紅外變像管,龔祖同為中國光學玻璃的試制與推廣生產整整工作了7個年頭。1957年他發表了《光學玻璃熔制的發展及有關原理》一文,對其7年來熔制光學玻璃的經驗作了科學的總結。
1962年,龔祖同奉命來到西安,協助組建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后,又創造了我國光學應用領域的數個重要的第一。
東北到西北:締造一個西光所
1962年3月,為發展中國的核武器,解決用于核爆試驗必需的高速攝影和耐輻照光學材料問題,在錢三強、王淦昌和張勁夫的提議下,國家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決定在西安成立一個以核爆試驗光測任務為方向的研究所。
國之所需,我之所向。龔祖同受命擔任所長,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副局長蘇景一任黨委書記。龔祖同帶領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數名科技骨干來到地處黃土高原的西安,在原中國科學院陜西分院所屬西安原子能所、應用光學所、機械所、半導體所、科儀廠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西安分所,1965年正式命名為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
據西光所一些已經是耄耋之年的老同志回憶,在建所初期,我們國家正處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工作條件異常艱苦,科研設施相當簡陋。在科研大樓未蓋好之前,各研究室都擠在邊家村老區的東一樓(宿舍樓)辦公,一間14平方米的房間放6-8張二斗桌,光學設計靠翻五位對數表,機械設計全用繪圖儀、鴨嘴筆,電路系統靠電烙鐵手工焊接。當時的一臺手搖臺式計算機就是所里最先進的設備。但是,大家工作起來是不分晝夜,辦公室燈火通明,常常直至深夜12點。
龔祖同重任在身,帶領這支年輕的研究所隊伍,一往無前,爭分奪秒,于1964年6月,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單片克爾盒高速攝影機和每秒20萬次高速攝影機,參加1964年10月16日我國首次原子彈試爆并圓滿完成光測任務。1966年11月,他們又研制出每秒250萬次高速攝影機,參加1967年6月17日我國首次氫彈試爆并圓滿完成光測任務。
核試驗轉入地下以后,在他領導下研制的電視變像管高速攝影機、雙路單幅變像管高速攝影機和納秒變像管掃描高速攝影機在1983-1984年三次地下核試驗中成功獲得早期中子流γ射線和X射線強度及能量分布的數據資料,為國家的核武器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此后的歲月里,在龔祖同的領導下又陸續研制成功速度從每秒幾十幅到2000萬幅的間歇式高速攝影機、棱鏡補償式高速攝影機、等待型轉鏡高速攝影機、同步型高速攝影機、狹縫式高速攝影機、變像管皮秒掃描高速攝影機、軟X射線皮秒條紋相機、變像管瞬時高溫議,以及不同時間分辨率的轉鏡型掃描高速攝影機和小型電影經緯儀等。
今天,光學纖維已經廣泛應用于光纖通訊及許多傳像場域。纖維光學是二戰后發展起來的光學分支,而在20世紀60年代初,纖維光學在中國還是空白。龔祖同以敏銳觀察和掌控科技發展前沿脈博的判斷力,于1962年就在新成立的西光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纖維光學研究室,組織、指導年輕的科技人員從設計制造拉絲設備做起,于1964年成功地拉出了中國第一根導光纖維,制成了第一根傳光束和第一根傳像束。隨后,為推動纖維光學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他又在1964-1966年間,陸續把拉制導光纖維的技術推廣到北京、南京等地。
中國的光學纖維工業由此起步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期,龔祖同開始梯度折射率光學的研究,創造性地從事自聚焦光學纖維及其在高速攝影中的應用方面的工作,提出用自聚焦纖維面板代替常用的微透鏡板當做網格元件的建議,西光所也研發了不少實用元器件。1978年,龔祖同在東京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高速攝影與光電子學會議上,發表了《錐形自聚焦光纖在高速網格攝影中的應用》及隨后的《自聚焦(變折射率)纖維在高速網格攝影中的應用》兩篇論文,獲得了國內外同行專家的一致稱贊,從而使我國纖維光學與高速攝影技術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當中國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時候,美國光學研究同行對于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在高速攝影方面的成就極為贊賞,授予龔祖同1981年度國際髙速攝影photosonics獎。
由于龔祖同在高速攝影與光電子學方面的杰出貢獻,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授予的技術重大貢獻先進工作者稱號,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在“現代國防試驗中的動態光學觀測及測量技術”中的7名個人獲獎者中名列第二。
在龔祖同的支持和指導下,1986年我國第一部大型基礎光學教材《光學手冊》問世,內容之新、分科之全均居世界同類書之首。
龔祖同一生不斷進取,從不停步。他活到老,學到老,探索到老。直到暮年,還抱著物質無限可分的信念,著力探索“光子的結構”,與物理學家丁肇中和錢學森通過書信討論“光子結構論”與“集成光學”的發展問題,希望對光的二重性問題有所貢獻。
善于育人:言傳身教,薪火相傳
龔祖同一生不僅治學嚴謹,而且善于育人,培養了我國新一代的光學專家,包括干福熹院士、母國光院士、劉頌豪院士等,而侯洵院士、薛鳴球院士、牛憨笨院士更是在龔老親手培育的西光所沃土上成長起來。
而早在抗戰時期,他就在自己工作的工廠里設過“龔祖同獎金”,獎掖后進,培養人才。
愈到晚年,他對此關切愈甚。1983年,他以79歲高齡,不辭長途跋涉,不畏酷暑,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九系為研究生講授"高速攝影概論"達半年之久。
“1985年底,當他僵臥病榻,靠鼻飼維系生命的時候,仍然關心研究所博士生的招收情況。”侯詢追憶道,“龔老,埋頭苦干、重視實踐,一切從祖國需要出發的精神,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正是在他年青時為適應祖國的需要從核物理轉向應用光學的事跡的感召下,我愉快地從等離子體物理轉向了高速攝影技術。龔老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西安光機所。”